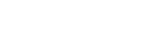北大教授罗新:你要是相信了,你就变成了它的囚徒、它的俘虏( 四 )
这个报告的核心意思是说你们家早就在我们这里,你们对我们具有先天的统治权。这个故事又跟拓跋鲜卑的史诗里面已有的关于迁徙的故事挂上了钩。鲜卑人很有可能是从大兴安岭地区走出来的,或者早期有这样的一些故事,但是一定要跟这个石洞挂上钩,这是非常困难的,是很难理解的。
当然我们不在这里做各种论证,我们从当时的周边环境、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历史上鲜卑和周边其他人群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来分析,他这么做是有必要的,是有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做了这件事情。后来的考古发现只不过论证了当初他的确这么做了,并不因此能够说明这个地方就是鲜卑人的发祥地。
所以从研究上来说,我们永远要处在怀疑状态,不要轻易地相信这个。你要是相信了,你就变成了它的囚徒、它的俘虏。
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在近代中国史学里边最成功的最了不起的例子是《古史辨》。很多朋友都知道《古史辨》,这是由以顾颉刚先生为主的一大批中国学者在20年代到30年代所做的一个伟大的工作。
文章插图
这些书把中国传统历史进行了反复地清理,把大量不属于历史的那些传说、神话从中国历史里边划出去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历史教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过去可能要从什么伏羲、神农讲起,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实际上是从夏商周讲起,甚至夏都很难讲起来了,夏存不存在到现在还是一个讨论的话题。
可是在他们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都相信有伏羲、女娲这些,在中国历史里边都是要讲的内容。是他们做的工作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有怀疑、有批判才能重建中国历史的系统。
很多人都说让材料自己说话,但是史料不会自己说话。史料不是透明的、不是无辜的,史料都是在特定的情形下由特定的作者有特定的目的为特定的读者所写的,所有的材料都是这样。
我们刚才看到的《开国大典》它是有特殊的情况,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特殊情况,你一定要去理解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有批判和怀疑的品德,才能够帮助你质疑过去的各种说法,提出一种抗辩、一种论辩。而只有抗辩和论辩才能够创造出改变的机会,这不仅是在我们的学术里面,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理性思维最宝贵的地方。
历史学家的神圣职责就是揭破各种历史神话,要知道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在揭破神话的同时,囿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限制,又难免自觉不自觉地制作各种新的神话,我们写的历史里边有很多是新的神话。
可以这么讲,我们熟悉的历史包含着大量的神话和假的历史,有一些将会被揭穿、被剔除、被取代,有一些会因为史料匮乏、证据单一,没有办法去证伪或者证实,就像刚才嘎仙洞这个问题,我们质疑它,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证伪证实你都做不到。
但是只要你具有了怀疑和批判这种美德,不仅可以勇于揭破那些神话来创造新的历史知识,而且还使我们在那些暂时难以撼动的新老神话面前保持警惕。我们可以不相信它,对它保持警惕,不要忙着成为它的俘虏。
我刚才讲的是批判与怀疑,现在我们讲想象力,想象力是我们历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美德。
历史是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经验,替代性经验就是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如果没有这个想象力,我们是无法理解前人的。
比如说这是秘鲁考古学最近的一个重要进展,他们找到了一个1200年前的贵族墓葬中最重要的贵夫人的头骨。他们用了各种技术、各种办法,把这个头骨复原为旁边的这样一个人的形象。
文章插图
这当中当然用了很多技术,专家们也认为这些技术是靠得住的。但即使是这样,专家们也一再说这个中间我们还是用了许多想象,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的一个秘鲁印第安人的头发来做她的头发。
所以这个复原当然很重要,如果我们整天看着那个头骨的话这个历史显得没什么意思。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立刻变得亲切起来,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想象力。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里边是两个学者对我们所熟悉的一篇文本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的研究。
《桃花源记》是一个文学作品当然没有问题,也是一个带有哲学寓意的作品,也没有问题。但是对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来说,这个文本可能还具有历史意义。也就是说,陶渊明写这篇东西应该有现实的依据,不然他没法想象出这样一个世外桃源。
推荐阅读
- Top10 清华、北大高居《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前二
- Top10 清华、北大位列《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前二
- 清华 《最强大脑》新一季脑王诞生,朱辉宇夺冠,北大终于战胜了清华
- 人造地球卫星 北大青年“数”说四史:“数”说“两弹一星”
- 教授 除了钱学森外,还有谁令美国惧怕不已?日本:有一位,能抵10个师
- 帕雷尔 沥青滴漏实验90多年才见证9次,熬走2名教授,究竟想证明什么!
- 乔教授 阿德莱德大学乔世璋教授JACS:道法自然,单原子催化剂活性位的新认识
- 人物 “北大韦神”高中班主任:愿公众少打扰他,北大多支持
- 人物 北大扫地僧冲上热搜:手提馒头矿泉水的他竟是斩获2块IMO满分金牌的数学大神
- 海南大学 新华全媒+丨牧海教授王爱民:为海洋生物安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