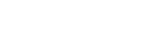善恶|周濂x何怀宏x刘玮x何家弘:我们该如何讨论善与恶?( 五 )
何家弘:何怀宏说他不知道未来,我就更不知道了。人类社会变成什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比较守旧的,我接受新东西的速度很慢。我的手机以关机为常态,以前一天开一次,不像有的年轻人一开就是24小时。我一开机大概开10分钟。现在我有微信了,一天可能开两次,有急事可能开三次,但是一般也就开机十几分钟。
我们的工作需要这些新科学技术,像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但它们又在冲击我们的司法活动,这是我们必须回应的问题。
从职业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司法人员?人工智能会不会让法官都失业?现在有互联网法院,还有 AI的法官。这个法官往往是一个女性,会发出很有魅力的声音,可以回答各种问题,但是它以后就完全可以代替法官来裁判吗?我们可以事先设计好规则,AI的法官就可以做出裁判。但它还代替不了人。有些裁判,包括我们情感的和道德方面的裁判,可能还得要法官来做。
人工智能这么发达,因为它主要靠的就是算法。据说算法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和意志,以后可能会脱离我们原来设计的预判和规则,这就比较可怕了。这究竟能走多远?我们希望,人类还有控物能力的时候不要让它走那么远,不能让计算机都代替法官,或者代替其他人的决策,特别是我们有情感,我们有伦理道德的思维分析。
作为一个活了这么多年的人,我还有另外一个对新科学技术的忧虑。科学技术首先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但同时也有它的弊端。为什么网络信息诈骗案件这么多?犯罪分子学习科技可能比老百姓学的还快,这也是我的忧虑。
我的另一个感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很多机能不使用就退化了。当然,年轻人退化得没那么快,但如果我们整个人类都如此依赖于这些机器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以后,人类的很多能力都慢慢减退了,我们真的就不如那些机器了?这想起来是很可怕的。像何怀宏教授讲的,人生里的很多东西不是你能决定的了,特别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只能跟着走。到时候,所有法官都变成人工智能法官了,可能我们也没办法吧?我们也只能跟着走,希望这一天来得晚一点。
刘玮:两位何老师刚才表达的基本态度还是忧虑的,感觉人还是被动的存在。周濂做过一个讲座,是说人的思维其实就是一种算法,这个观点会不会稍微乐观一点?
周濂:刚才我边听两位何老师聊人工智能和生化技术,边翻看手中的这本《关于善与恶的对话》,我在想,在不久的将来,这本书中的很多主题可能都会消失了。我特别想把何怀宏“人类还有未来吗?”的“问号”拉成“叹号”,但是好像我没有这个能力。
比如“生和死”的问题,有人预言,2049年人类就可以永生了。比如,“幸福”的问题,一旦我们真正发明出快乐机器,在大脑当中插一个芯片,直接进入“虚拟人生”的状态,就可以过自己想过的任何生活。这样一来,这些伦理学的话题似乎就都失去了意义。
打个比方,刘玮喜欢足球,他可以选择过梅西的生活;我喜欢篮球,就可以扮演乔丹。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过自己想过的任何生活,曾经遥不可及的幸福生活唾手可得,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似乎预示着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
但是,我担心这会对人类生活造成一种“连根拔起”的伤害。因为所谓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不正是体现在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系列沮丧、挫折、痛苦,以及偶有所得的那种快乐吗?当所有的挣扎、痛苦和努力都可以被一笔勾销时,我们可以即插即用、过上想过的任何生活时,不同类型的生活的好与坏,个体的自由选择,以及由选择带来的代价就都失去了重量。“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句话将真正成为现实,这个未来一点都不美好。
从政治哲学角度来说的话,更是如此。我们刚才反复在谈自由平等这些价值,它们曾经塑造了过去几百年的人类社会。福山在2002年写过一本《我们后人类的未来》,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三部曲当中也谈到了类似的忧思。他们的一个共识是,一旦人类真的实现永生,并且在未来创造出超人类,那只会让少数人获得永生的权利,让少数人拥有可以凌驾于众生之上的那种智力和能力。这将对人类的伦理、社会和政治秩序造成巨幅改变。
这样一来,人类将会迎来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尼采预言的“超人”就在字面意义上成为了现实。但是,刘玮应该很了解,尼采所谓的“超人”并不是一个不同的物种或一个更高级的种族,超人就是人自己——一旦他学会了肯认他真正所是的那个人。这也就是说,尼采的“超人”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成其所是”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成其所是,什么叫成其所是?这要认识到你的本性和潜能,并且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来实现它们。这个过程艰辛无比,但也乐趣无穷。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AI和生化技术,所有的这些努力似乎都可以唾手可得。
推荐阅读
- 挪红美食|善恶终有报:“大金羊”的未来三年,一切都是命的安排
- 豆瓣|豆瓣9.1,李准基黑白善恶难辨,四集三次大反转很高级
- [肿瘤专家高文斌]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改善恶心、呕吐的七大饮食诀窍
- 铁牛星座■为人正直,爱情中对欺骗零容忍的三大星座,善恶分明
- 哈利·奎恩■《猛禽小队》:善恶冲突下,反派也会冒险成为英雄
- [王宝强]马蓉被质问“坏人为什么还这么快活”,她回怼网友分不清善恶
- 『叶子猪游戏网』梦幻西游:千哥15技善恶神马改书 紫禁城更新须弥核武谛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