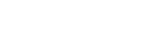善恶|周濂x何怀宏x刘玮x何家弘:我们该如何讨论善与恶?( 二 )
一个独立的个人满足自身的欲望就是善——就像我们说善待自己,这种善并不能作为一个社会和群体的标准。一般来说,利他是善,利群是善,利己不一定是恶,但不是善。这个标准还是太过抽象。不同的群体对善和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群体有自身的利益,他们是会互相冲突的。
除了法学家和小说家之外,我还在国际足联担任道德委员会的委员。有人会问,足球有道德吗?足球本身不是一种很高尚的体育运动,若太讲道德可能就没法玩了。但是,就像何怀宏说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足球里的一些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在绿茵场上是被允许的,但这需要底线。国际足联的道德委员会其实不负责管运动员是否踢假球、裁判员究竟有没有吹黑哨——那是纪律委员会要做的事。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反腐败——查办国际足联和各国足协官员的道德问题。
文章插图
何家弘
周濂:我研究政治哲学,同时也做伦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何怀宏说,”好“(good)就是我们追求喜欢的东西。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这两句话:第一句是“这件事情是好的,所以我想要去做它”,第二句是“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我应该去做它”。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做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了很强大的内驱力。我有欲望去实现它,但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反过来说,对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对(正当)与好(善)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张力,它们是伦理学中很重要的一对概念。
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伦理学跟政治哲学的一个概念区分。伦理学追问的是“我如何能够过上一种幸福的人生?”这里的关键词是第一人称单数的“我”以及“幸福”。政治哲学追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这里的关键词是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而且首先追问的是“对”或者“正当”,而不是“好”或者“幸福”。政治哲学要在规范性的意义上追问“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于是,这就出现了幸福与正义之间的张力。我个人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幸福,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正义。当然,我们是谁?我们因为什么而成为我们?这又是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
接着何怀宏的观点往下说,过去100多年来塑造中国和西方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何老师认为是平等。我认同这个看法。回想一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有一种思潮:我们应该追求政治上的平等——每一个个体,无论贵贱贫富,都有平等的权利去表达自己对于公共事务的想法,去伸张个体的利益。与此同时,另外一种思潮则追求经济意义上的平等。当然,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平等最终还是会反映为政治上的平等。进一步来说,在追求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过程中,最终会导致在整个社会观念上,我们把追求平等当作一个非常核心的目标和价值。
今天我们发现,平等意识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毛细血管当中。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们都在追求更进一步的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和阶级平等。但是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托克维尔早在180年前就针对人们对平等的追求提出了自己的忧思。他认为,在一个等级制度深入人心的社会,再大的平等人们也会视而不见。反之,在一个平等意识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再小的不平等人们也会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毋庸置疑,平等是一个好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处于一种追求平等的加速过程中,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最后我想接着何家弘的话说一句,他刚才谈到善恶的标准,对于伦理学和哲学的研究者来说,我们可以相对安心地驻留在“非善非恶”或“亦善亦恶”的灰色地带,进行所谓的哲学上的玄思,让对话和思考无尽地进行下去。但对于法学工作者和实践来说,他们必须要做出善恶的判断。这种当下的判断是非常艰难的一种实践。
2
面对犯罪行为,
我们要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
刘玮:何家弘老师能不能接着周濂老师谈到的话题说一说:法学工作者对于善恶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它是道德的底线吗,就像何怀宏老师提到的底线伦理?
何家弘:法律不是一个很高的社会性行为标准。我们平常说,“法眼看人低”。从法律来讲,这里的“人”都是社会上道德不是特高尚的人,所以我们才需要制定这些规则。如果一个社会中,个体成员都是非常高尚的,那我们大概不需要法律。我们有了伦理的导向,人们会把社会关系处理得很好。但在现实的案件中,我有时候却会很困惑。
推荐阅读
- 挪红美食|善恶终有报:“大金羊”的未来三年,一切都是命的安排
- 豆瓣|豆瓣9.1,李准基黑白善恶难辨,四集三次大反转很高级
- [肿瘤专家高文斌]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改善恶心、呕吐的七大饮食诀窍
- 铁牛星座■为人正直,爱情中对欺骗零容忍的三大星座,善恶分明
- 哈利·奎恩■《猛禽小队》:善恶冲突下,反派也会冒险成为英雄
- [王宝强]马蓉被质问“坏人为什么还这么快活”,她回怼网友分不清善恶
- 『叶子猪游戏网』梦幻西游:千哥15技善恶神马改书 紫禁城更新须弥核武谛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