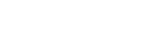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清史#孙江:日本的“大元史”与“新清史”,( 五 )
历史叙述是将“不在”的过去呈现于“现在”的行为 , 根据有限的史料在证据和可能性之间进行推论并得出不至乖戾的结论 , 这种工作十分不易 。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历史哲学的问题》(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1892)中认为 , “心理学是先验的历史科学” , 人很容易将自己的情感和意识投射到研究对象上 。 受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之影响 , 齐美尔在《历史哲学的问题》第二版(1905)修正了这一看法 。 但是 , 即便每一位历史书写者自称价值中立或价值悬隔 , 个人的情感和政治意识对书写行为还是会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 。 围绕“新清史”的争论即是如此 。 争论双方的焦点似在“汉化”——历史上的中国轮廓 , 实为“民族”——现实中的中国国家 , 除了冈田和杉山外 , 几乎没有一个“新清史”的拥趸会否认“汉化”的存在及其强大影响力 。 吊诡的是 , 中国学界在拒斥“新清史”的同时 , 却在拥抱杉山的“大元史”;在抵制“内亚”视角的同时 , 又在追逐“中央欧亚”的新潮 。 按照其逻辑 , 应为后者 , 而非前者 。 撇开这点不论 , 对立双方围绕过去的认识无疑都有着显明的当代性和政治性 。
杉山正明说 , “我们绝对应该避免以现代的状况或概念、印象为依据 , 来解释过去的历史真相” 。 是为正论 。 然而 , 杉山唯一一本学术专著《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的书名 , 即明显透露着作者的偏误 , 据说该书名直译是汉文“蒙古国与大元国” , 在蒙古人统治下 , “同时代使用汉语的人说‘大元(国)’ , 使用蒙古语的人说‘大蒙古国’(ulus——引者)” , 可见“大元国”即“大蒙古国”(大モンゴルウルス=Yeke Mongγol ulus) 。 显然 , 由于作者刻意强调元“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 结果把两个同义词混为一谈了 。 杉山贬抑汉文化 , 称册封体制、儒教文化、汉字文化等在东亚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和制度散发着自私的优越主义气息 。 借用他的话 , 这不正是以“现代的状况或概念、印象为依据”吗?所谓“现代的状况或概念、印象”是指基于对后民族国家的信念 , 试图打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 。 杉山反转的中国历史叙述隐约含有意欲超越现实的企图 。 杉山知道有被如此理解的可能 , 故而将论题严格地限定在“过去” , 只是偶尔会不经意地冒出几句惊世骇俗的话来 。 冈田则不然 , 其晚年编辑的著作集将以往文章写作“中国”的字样一律改为“支那” , 文中充满偏见的议论令人质疑其历史学者的身份 , 因而被杉山讥为“天马行空” 。
欧立德在为冈田英弘著作集撰写的出版推荐词(截取回忆文章的一段话)中说:“冈田英弘是全球史出现之前的全球史学者 。 ”全球史(global history)确切的含义应理解为“全球史学” , 正如global这个形容词所表征的 , 它研究的对象并非自明的 , 有关它的叙事是一种具有“未来”指向的行为 , 全球史研究面对现代历史学的重负 , 在迈向消解西方中心的国族叙事上关注空间上人的移动、物的移动所形成的人群关系 。 蒙古帝国打通东西交通 , 使欧亚大陆的东与西曾经存在的历史发生了断裂 , 这是事实 , 但如果进而说开启了“近代”世界历史的话 , 它和大航海后出现的近代世界历史到底是什么关系?杉山自身其实也很恍惚 。 后者之所以被视为近代世界历史的开端 , 是因为形成了由世界市场、世界认识、殖民统治等构成的具有实在性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 。 宝力格在关于杉山正明的书评中曾指出 , 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人的病态 , 只有游牧文化的攻击力量才能使其复苏和复兴 , “杉山正明(和冈田英弘)的世界史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写的 , 游牧民或蒙古人只是他们批判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的‘战争机器’而已 。 ”这道出了冈田、杉山二人之研究的当代性和政治性:通过反转中国历史叙述 , 曾经受中华文明支配、后又受欧美抑压并咀嚼过战败的作者在历史意识上获得了想象中的解放 。
推荐阅读
- 《街舞4》:淘汰日本编舞师,敲打黄潇,张艺兴做出正确选择
- 型男主播闪电宣布退社!弃电视台高薪转职大学研究员…震惊全日本
- 日本变态真人秀:全裸被监禁15个月,生活全被直播
- 动听故事会17岁扫厕所,23岁日本出道,她才是“央视一姐”
- 这位日本玩家火了,因太臭影响比赛,被赛事主办方吐槽人形粑粑!
- “爱国青年”张玉安:上节目暴怼日韩,直言日本嘉宾该跪着说历史
- 7部日本恋爱综艺推荐,第一名竟然不是《双层公寓&恋爱巴士》
- 日本跨年节目铁粉观众大迁移 重新解构电视产业的大众传播学
- 日本5万人电视游戏投票结果出炉 你喜欢的游戏上榜了吗?
- 日本节目组跟拍二手PS5能卖多少钱?一年过后价格反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