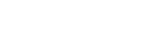鲁迅与4个女人扑朔迷离的感情 鲁迅几个老婆( 四 )
于是,像子君那样勇敢的许广平,向鲁迅刮起了爱的飚风 。
不慑于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
——1925年10月,许广平《同行者》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
——1925年10月,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
爱情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神的力量,它如同波提切利名画《维纳斯的诞生》里的风神,吹开枯枝上的花,引领肉身飞翔 。在许广平爱情风力的猛烈吹拂下,鲁迅终于不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当许广平在他“老虎尾巴”的书房里主动握住了他的手,鲁迅终于展颜一笑,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同乘车南下 。鲁迅受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先回广东老家 。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 。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朱安与鲁母依然住在北京西三条的家,由鲁迅供给生活用度 。
两人的结合,受到了诸多的舆论攻击 。
向来鼓吹文明与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撰文抨击鲁迅此举是“一个道貌岸然者的‘色情’私奔”;一封署名为“崇拜鲁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则说:“鲁迅先生,昨与某某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警戒之……”
尽管,许广平订下了同居契约:“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 。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然而,鲁迅在两人结合的初始,仍带着肉身的沉重与思想的禁锢,“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刘小枫语) 。他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称其为自己的“助手” 。朋友许钦文邀他们到杭州,为他们补度蜜月,鲁迅却让人预定了一个3人间,嘱咐许钦文:“白天有事,你尽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于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别扭:鲁迅与许广平分睡两边床,许钦文作隔山,睡在中间床 。
当然,沐浴在爱情中,鲁迅也焕发出一股子少年狂 。一次,在越秀山游玩,鲁迅忽然要抒发爱情与青春的冲动,他在许广平及几个朋友面前意气风发,纵身一跃,跳入身前的一个小土堆 。但是结局很尴尬,他碰伤了自己的脚,一拐一拐地出来,数月难愈合——毕竟年岁不饶人啊 。
在许广平怀孕5个月后,他们终于向亲朋好友公开了同居事实 。
1929年9月,海婴诞生 。鲁迅以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身份,沉浸在欢悦之中 。那日清晨,鲁迅手持一棵小松树,把祈福与感恩之心,轻轻放在母子俩的床边 。
生命的怒放与生命延续之喜悦,催开了鲁迅性情中极为温柔的一面 。他用温度计给海婴的洗澡水量温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给日本医生坪井写《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
鲁迅在《芥子园画谱》上题诗致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
在鲁迅的生命中,许广平充当了诸多角色:学生,秘书,精神战友,生活伴侣 。在生活与工作上,物质与精神上,承担起了事无巨细的责任 。为鲁迅查资料,找参考,抄稿,记录谈话,保管文稿,接待来客,打理家务,安排生活用度……
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做一个文学家的妻子,是很难的 。”除了形而下的难,还有形而上的难 。正如卡夫卡先后两次与菲莉斯订婚又解约,菲莉斯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牺牲品的角色 。作家对爱情虽是渴望,但对婚姻却有一种天性上的拒绝 。作为一个严格要求独立精神与个人私密创作空间的异类,他难以接纳同一个人(即使是“妻子”)长期侵入到他的空间之中 。刘小枫解释卡夫卡两次解除婚约,便是要掐断与外界的频道,“保持自己的天堂” 。而鲁迅,早在《伤逝》里,就安排了子君的离开与死去,也正是一个作家(涓生或鲁迅)在遭遇“存在与爱情”困境时,表现出的自私与保留自我世界的需要 。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的日子,除了会客,鲁迅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上,夜以继日,焚烧自我 。就其情感生活来说,从一个爱情虚无主义者与爱情怀疑论者,到在一桩婚姻中相安近10年,这不能不说是降临在“绝望的存在者”鲁迅身上的一个奇迹 。当然,也是因为许广平的福祗降临于鲁迅——“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 。”
推荐阅读
- 清朝皇帝过年旧俗 与群臣分食不加任何佐料白片肉
- 佛教的“卍”与纳粹标志“卐”之间有何关系?
- 风尘才女寇白门为何不惜与出轨情人玉石俱焚?
- 孙二娘嫁给了谁?母夜叉孙二娘与张青的爱情故事
- 刘姥姥与巧姐的联系 巧姐为何也是十二金钗之一
- 平阳公主与大将军卫青结合 真的是政治联姻?
- 中国历史上喜欢与和尚私通的四位皇后
- 揭秘武则天野史 武则天与她的男宠们
- 揭秘东皇太一与帝俊之间是什么关系
- 潘金莲为何背着西门庆与琴童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