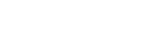鲁迅与4个女人扑朔迷离的感情 鲁迅几个老婆( 二 )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割席,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 。搬家之前,鲁迅问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 。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言语十分自卑凄苦 。
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即“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 。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 。饭间对话,也无非问菜味咸淡如何,答应者或点头,或曰“是”与“不是” 。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不穿,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不穿——鲁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条胯下之棉裤!母亲问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摇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 。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点心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 。其实这种点心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能吃到?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 。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这时,朱安真如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 。鲁迅有了海婴后,朱安面露喜色,为自己“无后之错”略微感到解脱 。还想着,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
1944年,唐弢等人为保存鲁迅遗物,劝阻出售鲁迅藏书,到北平逗留 。由鲁迅学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访朱安 。此时的朱安,已是白发苍苍,敝衣霜容,生活贫苦 。朱安禁不住冲着来人说:“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声呐喊,犹如杜鹃滴滴啼血 。她曾经是鲁迅的礼物,最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而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妻子 。呜呼悲哉!虽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朱安无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与痛苦 。其一种冷遇与痛苦,直接来自鲁迅 。鲁迅虽曾说自己也是“陪着作一世的牺牲”,但他后来有许广平与周海婴;而朱安做了一辈子无怨无尤的家仆,坐了一辈子无夫无子的冷宫 。终其一生,鲁迅对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 。在一生受囿于旧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个 。
(附:这时期,鲁迅写作《呐喊》、《野草》,有满腔的忧愤与苦闷,希望与绝望 。此间,他写及的女性形象多为很有生物爆发力的,并且语感紧绷,姿态压抑肃然 。)
二、鲁迅与羽太信子
学者孙郁说: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 。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 。从八道湾迁至西三条胡同,是鲁迅大家庭理想的破灭,从此,他与多年相敬相亲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
鲁迅与周作人,一直兄弟怡情,鲁迅对二弟的照顾与启蒙,真真切切地“长兄如父” 。周母曾说:“三兄弟住在一起十分友爱,曾经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说,兄弟永不分家 。”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原因,疑云重重 。但大致上,直接导因是因为:羽太信子 。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
作人
七月十八日
兄弟两人此段时间里的日记都语焉不详 。周作人事后撕去两页日记,对个中原委,周作人说:“不辩解 。”“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 。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 。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多年来,有众多学者或好事者纷纷揣测鲁迅与羽太之间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饶舌 。
推荐阅读
- 清朝皇帝过年旧俗 与群臣分食不加任何佐料白片肉
- 佛教的“卍”与纳粹标志“卐”之间有何关系?
- 风尘才女寇白门为何不惜与出轨情人玉石俱焚?
- 孙二娘嫁给了谁?母夜叉孙二娘与张青的爱情故事
- 刘姥姥与巧姐的联系 巧姐为何也是十二金钗之一
- 平阳公主与大将军卫青结合 真的是政治联姻?
- 中国历史上喜欢与和尚私通的四位皇后
- 揭秘武则天野史 武则天与她的男宠们
- 揭秘东皇太一与帝俊之间是什么关系
- 潘金莲为何背着西门庆与琴童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