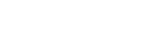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道家乡菜是啥说说你家乡的那些味道( 二 )
漂泊于外,每于深夜饿醒时,脑子里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味道,便是它们。
张血旺顾名思义,张血旺是个卖血旺的。
隔壁镇有个屠宰场,每天都会把几大桶新鲜猪血留下来,只供应给他一家店铺。
张血旺的店在小镇最繁华热闹处,只一间门面,纵深十几米,紧挨着摆了十几张小方桌。进门两口砖砌的大锅,花白头发稀疏的张老头永远系着围裙,站在灶边上。一边拿把大勺操作,一边对客人们笑脸相迎。
从早上到傍晚,灶里的火从不熄,但从没人见过他锅里的汤开过。
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煮出来的血旺才能比豆腐还嫩,入口柔顺,往红油碟里一蘸,咸鲜爽口至极。
猪血在盆里时还是鲜红的,一下锅,顿时烫成暗红色。若有新客来时,张老头便从锅的左边舀起一碗送上桌。
要是没有新客来,张老头便会舀上一大盆,离开灶台,为每位客人面前的碗里加上一勺血旺。
张老头只卖血旺,其他什么都不卖。按他自己的话说,也就只会做这个。
妈妈最爱吃血旺,连带着我自小也跟着吃了不少。
一来,血旺的确好吃,另一个原因则是便宜——两块钱一碗,不够还能加,包管吃饱。
在那个穷得一下雨就要上房补漏的年代,每次赶集吃什么都有讲究:不能太贵,也不能太难吃。
性价比极高的血旺汤自然是不二选择。
可也正因价格太低廉,它也被许多人排除在食谱之外。所以常常走进张血旺的店里,在座的几乎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一碗血旺一碗饭,兴许还会倒二两小酒,自有独自熏然的乐趣。
年轻人是很少见的。
我也有好几年没吃过了,上个月回来,某天莫名就想起了这道算不上菜也算不上小吃的吃食,就和妈妈说,要不哪天去尝尝?
妈妈说:“都关门一个多月了,以后是吃不成咯!”
原因是前段时间忽然爆发的非洲猪瘟,我们这里虽然暂时没有感染的病例,但政府加强防范,把周边这几个乡镇的屠宰场都取缔,重修了一座新的,统一管理。张老头再也拿不到新鲜猪血,自然就关门了。
看来,真如他所说,除了血旺,也就不会做别的了。可他唯一会的这门手艺,却被整个小镇的人公认是最好的。
现在,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蔡瞎儿蔡瞎儿是回民。
我们这回民极少见,据说三十多年前,他就搬到我们镇上来了。
蔡瞎儿不是真瞎,只是近视,矮胖身材,戴一副瓶底似的眼睛。可能那年头小镇里戴眼镜的少,就得了这么个外号,叫到如今。
蔡瞎儿在镇上开了家羊肉汤馆子,开了几十年,只有两样菜:粉蒸羊肉、羊杂汤。
粉蒸羊肉肥瘦兼半,面上撒一层焦香的辣椒面,几粒葱花、几片香菜叶,红绿搭配,颜色喜人。
羊杂汤则如其名,心肝肚肺早就煮熟备好,食客点上之后,在滚开的羊骨汤里一烫,滋味便出了。
但从小到大,我对蔡瞎儿的名头听得够多,他家的东西却没吃过几回。
贵。
在小时候的那些年,吃肉都得按计划来,何况是羊肉。偶尔去吃过一两回,接下来的大半年都对之念念不忘。
每次随父母赶集路过蔡瞎儿的店,闻到店里飘来的香味,都忍不住扭头多看几眼,悄悄咽一口唾沫。对店里坐着的食客们,羡慕得很。
我不是个例,对小镇上的许多人来说,一年也难得进店吃几回。以至于能坐在蔡瞎儿的店里悠然的吃羊杂汤,变成了一件体面事。
常能听到大家开玩笑说:“听说你今天打牌赢钱啦?走走走,吃羊杂汤去!”
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近些年羊杂羊肉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物了,蔡瞎儿的生意也比前些年好,前年还把旁边的一个门面也盘下,店面扩大了一倍。
前几日回家,便去吃了一回,和妈妈两个人,吃得憨饱。结账时还不足一百元,和记忆中的昂贵完全不同,让我有些感慨。
大概那些年留下的记忆,早在脑海里烙上了深深的印子。
老街抄手每次回家,老街抄手是必须吃的。
小镇统共也没几条街,还有老街新街之分。镇上的店铺大多没有招牌,‘老街抄手’的名字,也不知是哪个食客第一个叫出来的。
店主人是个性情豪爽的老婆婆,六十来岁,经常能与那些进店的熟客大声谈笑,开些少儿不宜的玩笑。就算最能说会道的男子进来,三两句过后也还不上口来。
她家的抄手皮薄馅儿大,佐料不多,无非油盐酱醋、葱花红油。口感酸辣咸兼备,一碗抄手最适合一口气吃完,酣畅淋漓!
推荐阅读
- 最新消息 麻省理工学院研发可编程数字纤维 有内存传感器和人工智能
- b《心动的信号4》官宣阵容,baby加盟,郭麒麟、宋祖儿惊喜现身
- 路透 《萌探》最新路透,那英、杨紫、宋亚轩、黄子韬的造型太搞笑了
- 太空飞行 鱿鱼宝宝和“水熊”将成为美国宇航局最新的微型宇航员
- 全世界 全世界最恶臭的花正走向灭绝
- 万人 罗志祥最新综艺节目暂时停播,因不到5万人观看,他凉了吗?
- 最新消息 象群走出昆明密林在田间踩踏:现场可见有9头 正从山坳里引出
- 综艺节目 当下最受欢迎的综艺大盘点,《极限挑战》排第二,它却排第一
- 杨紫 干最重的活、挨最狠的骂,陈赫李诞明明比杨紫干活多,为何被骂?
- 王霏霏 鲜厨解锁情侣套餐,王霏霏说在节目中收到这辈子最多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