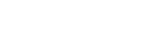船用起锚机 欲念起锚
当我第一次读到郑小驴的《上洞庭》时 , 我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地域色彩的湖南故事 。看完才知道 , 题目中的“洞庭”不过是虚晃一枪 , 小说中危险的当代生活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无关 。相反 , 题目中的“在路上”更能呈现出小说中恐怖紧张的气氛 ,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物总是在冒险、逃亡、复仇的路上 。记忆驴写的短篇小说里还有很多地方的风俗 。这些风土人情曾经为小说的气质定下基调 , 如今却被作者抛弃 。“乡土”的书写已经转化为“时间”的记录 , 作者和他的故事都在经历着“出域”的过程 。
去洞庭
小说《去洞庭》的核心是一个出轨复仇的故事:外卖员小耿强奸了精神错乱的张格 , 然后开车送张格去洞庭却遭遇车祸;古野对小说家连岳不忠 , 被丈夫史倩发现 。为了报复 , 史谦开车把古野送到了连岳的住处 。逃脱了警察追捕的萧庚得到了上司史谦的帮助 , 听从了史谦的意愿 , 劫持了小说家连岳去见史谦 , 却意外导致小说家溺水身亡 。小说的每一节都围绕故事中的某一个人物 , 交替叙述 , 就像电影中的一个分镜头 , 让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人生历程向读者敞开 。聚焦板块的方式则释放了叙事的时间限制 , 以辐射的方式开启了五个人物的生命历程 。一个关于欺骗和复仇的故事涉及五个现代生活的冒险 。
在这里 , “冒险”并不单纯是一种比喻 , 也不仅仅是指五个角色都在不断逃离原来的生活区域 , 更重要的是 , 这些角色都具有现代的冒险性格和现代野心家的含义 。
父亲患病后 , 农村青年肖耿寻求生财之道 , 既好斗又暴虐 。来自华北的漂泊者女孩张戈 , 决心只身前往北京 , 热衷于打造中产生活;当然也包括对艺术充满热情、充满浪漫幻想的女青年古野 , 以及在商业上东奔西跑、在赌场上挥金如土、爱征服沙漠的商人石倩 。还有连岳 , 一个孤独而又自恋的小说家 , 靠着古野的支撑和情感慰藉 。这些现代野心家的面孔都很熟悉 , 都有安娜·卡列宁或者莲莲的影子 。19世纪小说的传统就是这样的浪漫传奇 。评论家特里林曾指出传说和冒险故事与19世纪的亲缘关系 。在这些小说中 , “必须有一只巨大而有力的手伸向这个世界 , 打破看似无望的套路 , 选择一个主人公有着复杂而危险的命运” 。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有着无穷无尽的动力 , 他们去北京、东莞、西藏、东北、洞庭、长沙寻找爱人 , 追逐名利 , 驾驭自然 , 释放生命的能量 。核心复仇故事的前史 , 就这样被描述成五段不同的冒险 , 却有着相似的时代气质 。
但毕竟所有的冒险都被捆绑在一场情感的复仇中 , 小说的分段叙述又发散了故事的时间线索 , 使得强奸案、出轨复仇与人物的现代冒险发生重叠 , 所以人物的冒险无论是魔幻、浪漫还是惊险 , 都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 。这种情感复仇的不祥味道 , 也因为小说中嵌套的故事而更加强化——小说家在洞庭湖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出轨复仇故事 。一个哑巴男人几十年前在洞房里埋葬了他美丽的妻子和她出轨的伴侣 , 小说家被这个令人震惊的故事震惊了 , 并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小说;当他在琢磨一本洞庭湖的新小说时 , 报复他的商人和潜逃者已经在路上了 。偏僻水域的死尸 , 此刻正在发生的背叛与复仇 , 叠加在洞庭湖上 。
这样 , 小说文本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被引导向两个方向 , 一个是人物在地球上无限探索和迁徙的冲动 , 另一个是吓人的哑巴故事和湖底尸骨的召唤;作者一方面似乎想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 , 写下当代的生活是如何激起人物行动的欲望 , 另一方面又似乎想做一个死灵法师 , 邀请一个恐怖的故事幽灵回来施法 。两种叙述方式并不总是互相配合 , 有时还会消散彼此的意思:小说结尾 , 小说家在遇到商人史谦之前意外溺水 , 史谦没有像哑巴一样把妻子和情人扔进湖底 , 而是让妻子回去让逃犯萧庚把自己刺死;小说最后以张格手里的瓶子里的船的形象收场——模糊地暗示着一种渴望 , 要和一艘不会航行的船一起抛锚航行 。小说的意图和人物行动的方向一样 , 就像外力画出的圆 , 重力从湖底画出的圆 。
80后 , 回到19世纪 。
小驴出道时 , 他的短篇小说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1921童谣》和《痒》中用怪力混乱的神沟通历史暗流的写作 , 被批评家称为“幽灵般的叙述” 。但作者这几年的写作 , 似乎是在逃离湘中、湘地的文化因素——虽然会留下一些痕迹 。不知这是否与作者在人民大学作家班三年的研究生经历有关 。毫无疑问 , 小驴是被时代的生活主题所吸引的 。然而 , 这种与西方19世纪特定的现代感知和现代人格密切相关的“时代感”却能被小驴迅速接受 。毕竟 , 小驴也曾是一位地域色彩如此浓厚的作家 。
将19世纪的现代性确认为一种对现实现代生活的感知方式 , 与80后作家的观点相似 。石一枫(1979)、马小淘和郑小驴是一些年轻作家 , 他们的批评家热衷于讨论城市底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 。将他们与之前和之后的作家进行比较 , 可能更能反映出80后作家对于当下作为“漫长的19世纪”的延续的接受强度 。我们只要稍微回忆一下五六十年代以后的作家们对古典儒学、西方现代主义或中国革命史的理解深度 , 就可以理解这一点 。不仅作家 , 80年代的批评家和研究者也是这种历史意识的建构者 。正是批评家和作家的相互阐释和影响 , 使得此刻的中国被理解为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现代中国 。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例子也来自郑小驴 。80后批评家李晶把郑小驴早期小说的“鬼”和“焦虑”理解为另类的“青春”基调 , 但这种风格与“楚文化和沈从文的文学传统”的联系却“被压在了一边” 。也就是说 , 当代批评家有意识地剥离了作者的地域因素 , 批评家参与了作家的“去域化”过程 。
80后批评家的问题意识似乎是从现代范式下的历史认知中诞生的 。比如 ,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 杨的批评研究为什么是从重读路遥开始的;批评家们对城市中产阶级的困境异常敏感 , 这可能不是偶然的 , 正如《80后怎么办》中所显示的那样 。这样的问题不仅涉及到一代人的文化谱系 , 也涉及到当代历史在代际之间造成的知识断裂 。
【船用起锚机 欲念起锚】还是回到小驴的小说 。大约100年前 , 深受新文化感召的青年沈从文离开湘西 , 来到北京 。在对新文化的符号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认知和创造之后 , 他终于开始回望自己曾经想要脱离的“边城” , “赋予文学生命一种‘离域’的历史品质 , 然后在变化着的中国情境中‘重新嵌入’” 。并不是指望小驴重复沈从文的文化创作之路 , 百年后的文化结构和时代语境早已发生了转移 。只是两位作家也是带着湘楚文化的敏感和鬼魅气质走向文学之路 , 在自己的身上 , 在作品中 , 会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牵引和变化 。作为读者的任务 , 或许就是跟随、体验、确认作家笔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常态 。(刘)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