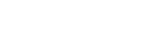令曾国藩父子“低头一拜”的人物( 二 )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曾国藩,又经过多年宦海沉浮的历练,深知“日中则昃,月盈则亏”的道理,意识到“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祸咎之来,本难逆料”,“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惟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 。这样,才能“持盈保泰” 。也难怪曾国藩对屠羊说如此崇拜了!这里,曾国藩感佩和心仪的是屠羊说内心的超脱与宁静 。
曾纪泽(1839—1890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子 。曾国藩死后,曾纪泽袭封“一等毅勇侯”,地位仍然十分尊崇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熟悉世界政治的干才,他被遴选去从事外交事务 。1878—1886年间出使英、法、俄国 。1879年因崇厚签订的《里瓦基亚条约》丧权太甚,举国哗然,清政府迫于舆论,拒绝批准条约,并于1880年派遣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兼充出使俄国大臣赴俄谈判,力图挽回损失 。面对如此不利局面,曾纪泽不避艰辛,决心完成“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使命 。他分析形势,认为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力已大受损伤,且与英国等国有矛盾,不会再对中国发起一场战争,俄皇与其外部丞相都有和平了结之意 。而左宗棠手握重兵,驻扎西陲,可以作为后援,因此,事情犹有可为 。经过一番艰难的斗争,繁复辩驳,终于于1881年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争回了部分权益和领土 。这是曾氏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一件事,为其生前身后赢得了美好的声名 。
时至晚清,政象纷纭,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朝不保夕之感 。1864年的曾国藩达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谓名既大,谤亦随之 。在他享有极大极高尊崇的时候,非议之音也纷至沓来,“左列钟铭右谤书” 。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轻 。
但是,在不久以后的中法战争和中法交涉中,曾纪泽的良苦用心就遭到了一次极为痛心的打击 。作为行走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臣,他有责任和权利向政府申述自己对时局的设想,曾纪泽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努力向最高决策者进献忠言,希望能为国家再争得一线生机 。本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中国的国力已经颇有些气象,而法国经过普法战争的失败之后,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清政府完全可以统筹全局,周密部署,在疆场上与之一决高下,在谈判桌上与之腾挪周旋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实在是太孱弱了,它既不能审时又昧于大势,只是一味地妥协退让,致使曾纪泽的真知灼见在中法交涉中没有发挥积极的效用 。交涉的不利结果和来自国内的训示让他懊恼,他深感自己的无力与无奈,思忖年华渐逝,鬓发已衰,他只能随缘了 。此时,陶彭泽闲静、淡远的人生态度自然令他心有戚戚了 。
曾氏父子都感到世事无常、祸福难测——“人间随处有乘除”,但他们生活的年代不同,人生遭际不一样,具体的人生态度也稍有差异:曾国藩位尊权重,深忌“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因此很超然——“万事浮云过太虚”;曾纪泽承袭父亲勋名,有才,但不能见重于当道,而政府举措失宜,中外交涉自是歩履维艰,处此情境,“一腔愤血,寝馈难安”,深叹“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似有听天由命的味道——“万事乘除问酒家” 。不同的人生态度影响了他们以后各自的行程:曾国藩谨小慎微,获得善终,死后谥号“文正”,备极哀荣;曾纪泽的主张因与最高当局的决策相抵牾,先是被免掉出使法国大臣兼职,后又被召回国,在京城做着不大不小的闲官,“不得当路之助”,颇不得意,郁郁以终 。
曾氏父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陶铸出来的精英,在时代潮流的冲击、影响下,他们具备了一些传统士大夫所没有的因素 。曾国藩是洋务派的地方首领之一,曾纪泽似乎走得稍远,他精通英语,目光新锐,持节外洋,在中外交涉中折冲樽俎,为国家挽回了些许权利 。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充溢着传统士大夫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仍属于传统的士人阶层,只是时代的风云变幻将他们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在晚清诡谲的政局中,他们本能地将思维指向旧有的诗书典籍和他们心目中的名人贤士,在那里寻找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
推荐阅读
- 吕芪的美貌令所有男人销魂 为何会变成女土匪?
- 令人震惊 人类史上被诅咒遗弃的五大家族盘点
- 孔令伟生平简介 孔令伟是怎么死的
- 中国也曾有“炮决” 曾国藩炮轰洪秀全尸体
- 青楼名妓颜令宾最后到底怎么死的
- 胡林翼劝说曾国藩当皇帝为何会失败
- 明朝倭寇多且不怕死 竟是因为这条禁令所导致的
- 嘉庆朝令人啼笑皆非的马屁 皇帝圣明教化了蝗虫
- 详细盘点那些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名将
- 涨知史!那些令人震惊的历史真相你知道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