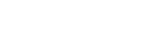生命之花起伏,如山丘
本文插图
在澳门艺术节上展演的现代舞《野花》场景 。 第三十一届澳门艺术节于2021年4月30日至5月29日举行 , 以“再出发”为主题 , 共推出20套节目 , 金星舞蹈团的现代舞作品《野花》为其中之一 。□ 黄礼孩
现代舞是生命的摇摆 , 也是心灵的形态 。 艺术打开意识的牢笼 , 通过身体的召唤被异化升华 , 在生命的相互交错中 , 舞蹈获得的触角延伸向天际 , 这正是身体创造美学的价值 。 上海金星舞蹈团的《野花》阐述了这样的当代舞概念 。 来自荷兰的编舞大师亚瑟·库格兰 , 作为前话剧导演 , 他给第三十一届澳门艺术节提供了一台陌生感的舞台作品 。 在艺术创作中 , 命运之绳将不同的人牵连在一起 , 比如这个作品的艺术总监金星、出品人汉斯、作曲克里斯帝安-迈耶尔、灯光设计王鹏等等 , 他们是隐秘王国里观念的存在之链 。 从意念到文本到舞蹈 , 再到澳门的演绎 , 《野花》形成一种命运之舟 , 多数人所不知道的航行 , 驾离预期的生活之岸 , 去往未知的海域 , 散发出体悟的波光 。
七十分钟的《野花》是一种激情的演绎 , 说是野花的无名与寂寞、磨损与挣脱、繁华与荒芜、爱欲与哀矜、奢华与梦想、敞开与觉醒、绽放与歌唱 , 但它也可以是别的事情 。 舞蹈因为抽象 , 所以模糊了边界 , 获得更多的语调与色彩 。 《野花》是散文或自然之诗 , 似乎是对所经历过的青春的怀恋 , 或者幻想另一种生命的存在 , 对都市迷失于浮华世界报以的沉思 , 从一场一场迷梦中醒来 , 重建对土地的回忆 , 返回艺术家一直致力寻找的场景 。
舞蹈从摆头开始 。 甩头 , 持续甩头 , 身体因情感的欲望产生意想不到的动作 , 从一个小摆动的节奏开始 , 整个舞台都处于从慢到快 , 快到慢反复的变化中 , 男子群舞的小幅度动作 , 女子群舞的大幅度动作 , 或女子群舞的小幅度舞蹈 , 男子群舞的大幅度舞蹈 , 他们重叠着进行 , 迂回地披上想象之花的外衣 , 时间的线条之歌就飞了出来 。 舞蹈是一个讲究动机发生的艺术 , 一个行动意象发展出多种肢体语言 。 《野花》是偶然动作选择的总和 。 甩头 , 小幅度变幻的舞蹈 , 接着是扭动胯部 , 摆动手臂 , 它是生命的摇曳 , 渴望挣脱生命之身的界限 。 在此 , 有什么样的生命状况 , 就有什么样的情感力量和角色回旋着振奋的身体 , 不断诞生出不同的思维 。 重复 , 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上上下下 , 重复的律动 , 作为一种时间、地点、节奏、光线在加强 , 它是在变化中被观众所接受 , 仿佛季节、植物、岁月、自然 , 那循环往复中的跳跃 , 几乎就是心灵曲线上的音符 。
舞蹈是闪亮的风 , 遇见 , 似乎有进入狂风中生活的迷惑 。 风吹过 , 起伏之间舞蹈如海浪飞出 , 思想之鱼把隐藏的东西带出来 , 那是一个奔涌的瞬间 , 摇撼世界的力量 。 空间的调度 , 不同的组合与构成 , 让舞蹈以速度捕捉到忧伤或喜悦、贫穷或富有、黑暗或明亮 , 这一切好像光晕中的野花 , 气味凝聚过来 , 比原野还真实 。 不停留在主题上才是有思索空间的舞蹈 , 如此的迎来送往才构成连接之桥 。 一出好的舞蹈 , 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 , 如果被猜到了 , 似乎还不够稀奇 。 比如“碗”的那个舞段 , 也是臆想不到的 , 有不少人喜欢 , 有“醉龙舟”舞蹈喷酒的影子 。 个人觉得以“碗”为道具这一舞段 , 长了一些或者显得多余一点 , 就像整出舞蹈的音乐加进来中国元素 , 多少显得有点刻意 。
较之舞蹈里“脱掉小西装”摆脱思想牢笼的隐喻或者“蒙克般呐喊”的困境表现或“情色之花”轻浮气息的描摹 , 都是当下生活或者环境的反映 , 充满忧虑:它们带来的不一定是新的绽放 , 也许是新的枯萎 。 对于一个有思考能力的艺术家 , 他们不希望表达拙劣的幻觉 , 呈现的应是“自然之法” , 提供解脱之道 , 也就是舞蹈要表现出令人惊奇的身体表象下的真实 。 场景切换是舞蹈戏剧化的元素 。 没有光束就没有舞蹈 。 在光的运用上 , 《野花》很有几何感与数字意味 。 无论硬质光或软质光 , 在舞台上都是变化的建筑 , 让舞蹈保持视觉的开放性 , 折叠出新的空间 。 《野花》的音乐节奏一直是高亢的 , 但高里有低 , 低里有高 , 就像十四个舞者的组合 , 起伏成为看得见的音乐 , 也就是节拍变成了动作 , 其激烈跌宕的强力改变着观众审美力 。 《野花》不是舞剧 , 没有剧情 , 但在芜杂的纠缠中暗藏着一种结构 , 从独舞到双人舞再到群舞 , 舞蹈处理了不同的关系 , 多个层面的关系才编织出旷野的生命意象 。 优秀的舞蹈背后有成熟的美学意识 , 它是一种可以看得见的图像 , 时空骚动又静止 , 仿佛格律之诗与自由之诗般的存在 。
推荐阅读
- 天生命好,旺夫旺钱财,能富贵满门的三大生肖女
- 未来十五天鸿运接踵而来,富贵之花朵朵开,大财进腰包的3大星座
- 6月爱情之花绽,桃花运大涨,3大星座步入爱情之路,幸福脱单
- 七月桃花别样红,爱情之花盛开,喜结良缘,脱单在即的三大星座
- 星历0611:天秤情绪起伏大 射手引导众人
- 多想把你从我的生命中移除,12星座如何忘记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