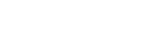天文这么有趣的事,先从看球幕电影开始吧!( 二 )
球幕电影在极大程度上还原了来自现实世界的真实感,又能提供一些超真实的体验。说球幕是天文馆立馆之本似不为过。
(小标题)天象节目数字化
是为了“科学可视化”
尽管距离鲍尔斯费尔德的发明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现代天文馆的运转方式仍然与最初的设计十分相似。与此同时,随着投影系统的技术提升和天文学研究的进展,天文馆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光学天象仪被替换成数字天象仪。
北京天文馆的数字工作室就是2004年随着新馆落成而成立的。宋宇莹介绍,之前的放映内容都是基于光学天象仪,只能模拟以地球为核心看到的星空。天象厅里的斗转星移,动的是天象仪。原理就像纸杯上扎很多孔,中间点亮一个灯泡,杯子一转,“星星”就跟着转了。当然,实际的光学部件要复杂得多,得让对焦、孔洞更精细,能模拟大的、小的、亮的、暗的各种星,还能闪烁……
2004年之前,天文馆的节目都是星空配上幻灯片,虽然也可以拼接成一个全景的影像,但全是静态的。“我们开始学习所有跟数字展示相关的制作技术,这简直就是另外一个行当了。不过,放映还是这个(球幕)环境。”宋宇莹说。
数字天象仪最初也只能投星空,最大的进步是可以任何地点为视觉核心投影,可以模拟在星空里穿梭,位置都是基于天文星表的。北京天文馆引进的数字天象仪原配的星空只能投实时画面,而且因为版权问题,不能在此基础上做节目。所以数字工作室又重新做了一套星空系统。“这是我们所有影片制作的基础。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数字工作室工作的重心,慢慢转移到在星空基础上加入更多科学可视化的内容。
什么是科学可视化?
宋宇莹解释:“比如要跟大家讲地球的磁场。受太阳磁场影响,地球在空间运行的时候,磁场会变形。变形成什么样子?如果只是在动画软件里‘捏’一个,它的运动状态不符合物理规律,那只能是‘哄小朋友’,毕竟我们不是做动画片。所以,必须要保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有产出的视频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依照科学的逻辑。”
《宇宙大爆炸》也秉承了这一理念,“每一个像素都有数据支撑”。
采访人员跟随他参观了数字工作室的机房,教室大的一间屋,被服务器占满,这已经超乎惯常想象的影片制作环境了。然而,整个数字工作室团队只有五个人,三个学天文的,两个学计算机的。
“我们的工作相当跨界,作为科普节目制作者,要把高深的科学知识可视化,还是这种沉浸式的播放环境。这些年最大的困扰就是与合作伙伴沟通,我们非常希望更多有理科背景的艺术生参与其中。”宋宇莹说。
生于1978年的宋宇莹,也是天文、计算机跨界。他谦虚地说,计算机就是个工具,人人都用,只不过天文学家是用来控制望远镜,或计算某些设想的物理过程。
(小标题)科学“搬运工”的日常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的天象厅数字科普节目创作团队负责人,宋宇莹也坦言被“催更”有压力。逛天文馆的多是亲子家庭,面对展品、展板中的天体物理知识懵懵懂懂,作为必选甚至首选项的“看电影”,对节目期待可想而知。
“一部片子周期差不多是两年,当然这只是制作周期,策划很早就开始了。比如《宇宙大爆炸》,从最开始有这个想法,酝酿了10年。之后慢慢积累相关的素材,还会储备一些相关知识。需要了解当前中国的宇宙学研究到什么程度,能够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技术支持。同时关注国际上宇宙学进展,是否会对之前的理论有一些推翻性的观点,总之要不停充电。”
“现在天文爱好者越来越多,对科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片子较之前的几部是跃了一个台阶,也圆了我自己一个梦。”宋宇莹说。
技术含量高了,并不代表不接地气。就像主题歌所唱:“暴胀吹出的泡泡宇宙/无数的足球宇宙/其中之一是我们的宇宙/更多的更多的足球/永远没有尽头……”
“只谈各种夸克、粒子,别说孩子,多数成年人听起来也会晕,不如用一个直观的描述,让他知道这大概是怎么回事。至于为什么是这样,如果真的感兴趣,可以再去看其他的相关资源。”宋宇莹解释道。
确如其言,采访人员在二刷之后,再去新馆参观地下一层的“宇宙穿梭展厅”,面对宇宙起源那一大面展板,之前似是而非的各种粒子图像显得格外亲切;暴胀时代、夸克期、光子解耦、第一代恒星点亮……这些线索在头脑中也有了全息的画面。
推荐阅读
- 吸血 10个奇葩有趣的冷知识, 公蚊子吃素, 只有雌蚊子才吸血
- 天文学 “宽视场巡天望远镜(MUST)”将落地青海冷湖
- 生猪价格 生猪价格正在下跌和上涨。为什么上升这么难?终于找到原因了
- 太阳系 地球拥有“130亿亿”吨水,这么多的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 物理学家 天文学中早已被推翻, 但还被普通民众视为常识的理论
- 中美 拜登遇到了硬茬,美元收割战略失败,金融独立自主就是这么硬气
- 节目组 豆瓣评分2.5,这档综艺节目就这么静悄悄地糊了?
- 团队成员 火星突然变暗27秒美国洞察号在另一世界记录了奇怪天文现象
- 太阳系 人类科技飞行222亿公里拍下一张照片,美国天文学家应该深思
- 天文 2021日食季:金边日环食来了!月食过后又是日食,是不祥之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