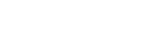你现在困在哪个围城里你会出来吗( 二 )
她们聊天的工夫,我就四处寻觅新奇的事物。我在堤道下的草丛里捕捉蟋蟀,又脱了鞋子,赤脚爬树去抓天牛。到了人家里我也不安分,好像凳子上有火炭,屁股总挨不住,不是在路沿的砖瓦里翻蚯蚓,就是在土墙里捅土蜂,最安分的时候就是蹲在墙根下看蚂蚁,直到祖母结束她的倾心之谈,开始呼喊我的名字。
我们是去舅公家,正事可不能忘。
“去人家里做客,去晚了,很不礼貌。”祖母说。
祖母的话,有些我听,比如这句,去人家里我总是早到。然而祖母的话似乎已经过时,人们对待客人的态度,和早到晚到并没有关系。重要的客人,姗姗来迟,主人也仍然等他开席。不重要的客人,你来或不来,也没有人在意。
但是祖母并不能预见这样的变化。她哪里知道,路上偶遇的熟人都要热情地拉她回家吃饭,有一天,骨肉至亲却会形同陌路?
祖母的话,我大多是不听的。走在路上,我总不安分,这个树丛里钻一下,那个水坑里踩一脚。祖母说:走路要走大路,做人要走正道。
祖母的布鞋是自己纳的千层底,剪的鞋面,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那鞋子还没我的鞋大。她小时候曾裹脚,尽管后来放脚了,还是成了个小脚老太太。
就在这条堤道上,九岁的祖母坐着花轿,嫁进了老杨家做童养媳。那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值得回忆的镜头。花轿晃晃悠悠,四个人抬的,我忘了问她,有没有喧天的锣鼓,有没有送亲的队伍,有没有凤冠霞帔红盖头。大概是有的吧,毕竟,老杨家那时候算是富足。
祖母没有读过书,一生劳苦,生养了三儿二女,38岁那年做了寡妇,门前清誉,至死未曾玷污半分。
这就是她的小脚走出的大路,她做到了。
世界在变,道路也早已修修改改,面目全非。什么是大路,什么是小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祖母那时候,路就那么几条,大家的标准简单、趋同,而现在,路网如蛛丝缠绕,千头万绪。我眼里的阴暗小路,却是他人飞奔的康庄大道。别人眼中的荒野戈壁,却是我心中的堂堂正途。
罢了罢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是。
三
沿着堤道前行,三溪港拐了个大弯,舅公的村庄便到了。我记得村口有一个高大的牌楼,但是忘了上面写的什么。是哪位节妇的牌坊,还是哪朝哪代的御赐,或者只是村庄的名字?
那时候我还小,对这种严肃的建筑并不太喜欢。长大之后再去,牌楼已经不在了。村庄里新楼林立,许是谁家建房拆掉了。
舅公是个驼背的老人,终日拄着一根手杖。后来我读《白鹿原》,读到白嘉轩折了腰杆时,想到的便是舅公的形象。白嘉轩折了腰杆,做人仍然硬气,舅公也是如此。他的双眼炯炯有神,口齿清晰,安排起事情来条理分明。常常拄着手杖照料菜园,饲喂鸡鸭。待人接物极有分寸,从不失礼,浑身散发出一种睿智而强悍的气场。
舅奶奶是个聋哑人,说话总是比比划划,咿咿呀呀。她并不是生来如此。祖母说,年轻的时候,舅奶奶是个教师,至于后来为什么变成这样,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大人们有他们的秘密,而我那时候对这些秘密也并无兴趣。
我从小跟着祖母长大,舅公和舅奶奶身边也跟着个小表妹。她的父母在外“躲产”,只得把她留给祖父母照顾。不同于我从小表现出的忧郁气质,小表妹活泼好动,热情礼貌。见了祖母就喊“姑婆婆”,见了我就喊“哥哥”,嗓门嘹亮,笑容灿烂。还像个大人一样端茶倒水,忙前忙后。
“十里不同音”,他们的口音与我们大不相同。我们的口音平实质朴,听起来有点土,他们语调上扬,多了些抑扬顿挫。我们管孩子叫“细人”,他们叫“伢子”。
大人们喝茶闲话,小表妹便拉着我去玩耍。溪流的拐弯处孕育了一片沙滩,溪水里有许多小小的贝壳。我们常常捡拾许多,临走时又挥手扔进了小溪里。
小溪、沙滩和贝壳勾起了小小的我一个梦想,我对小表妹说:长大以后,我要去看大海。
小表妹说:你看到大海之后呢?
我说:看到大海就坐大船。
小表妹说:然后呢?
然后,坐上大船就打大鱼……
四
舅公、舅奶奶和祖母相继去世,他们的稻田已经收割了。
小表妹嫁了人,算来已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离开的时候通讯还没这么方便,我们各自经历,各自成长,就算现在见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认不到。
现在,除了过年时长辈们还会走动一下,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走过那条堤道了。
然而,“种性强韧”,我们的身体里有着同一脉鲜血,那些遗传在DNA里的信息,却无法因时空的距离而斩断。
推荐阅读
- 速度 宇宙中比光速更快的四种“速度”,你都知道几个
- 男人帮 跑男、极限挑战、向往的生活,以这种方式“融合”!你期待吗?
- 召集人 张彬彬致敬李大钊,《28岁的你》正能量偶像解读伟人事迹
- 孕育 银河系中为何只有地球孕育出了生命这里告诉你答案
- 太阳 宇宙中所有星球都悬在空中,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这里告诉你答案
- 刘彦春 无论你负债多少,三年内都可还清所有债务!
- 地球 如果太阳燃烧完了,人类该如何生存?《方舟生存进化》为你解答
- 张震岳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加拿大paowang再添一锤,多人曝光记录
- 银河系 曲速引擎或能让人类飞出银河系,为何现在却无人研究?
- 铁矿石 全球最“值钱”的8大货币,美元直接垫底,前三名你们认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