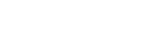你现在困在哪个围城里你会出来吗
昨天是我33岁的生日,33岁的我仍然一事无成,没车没房没有女朋友。也有女人对我表示好感,可不敢接招。我现在在一家马术俱乐部做总经理,听上去是不是很高端大气上档次?事实上我手下只有一个员工,三匹马。俱乐部在一个县级市,每天门可罗雀,面临倒闭。员工也是个和我一样的卢瑟,职位是马术教练。老板正打算把他开了,因为养不起两个人,当然被开的也可能是我。三匹马,一匹黑色的13岁骟马,以前是匹赛马,前腿受伤退役了;一匹6岁的栗色母马,右眼白内障,面临失明的危险;还有一匹5岁的栗色骟马,最强壮也最骜烈。因为没有生意,老板连草都不买,三匹马有半年无人照料,放在野地里几乎回归了野性。后来马场进了小偷,偷走了两台空调,老板才请了个教练。
这三匹马,踢人,咬人,来了顾客也做不成生意。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一地鸡毛。
然而,如果要说这是个围城,我被困在里面,我并不同意。
我小的时候玩过一个游戏,名叫“跑城”。就是在地上画一个大大的长方形,代表城池,里面再画“井”字样直线,代表城墙,一方守城,一方攻城。守城的一方,层层设防,攻城的一方也要逐个击破。
这个游戏在我看来,可以解释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限于篇幅和主题,这里只简单讲一下:中国文化如果用一个字概括,这个字一定是“守”,农耕文明,喜欢守,守着一亩三分地,守着老婆孩子。这座城池,先是守仁,仁守不住了,守义,义守不住了,守礼,礼守不住了,守法。现在宣扬法治社会,法就守得住吗?我不敢乱说,尽管法律允许我说。
我以为,我现在守的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守心。没错,我现在在看王阳明。
所以,如果说我在一座城池里,不是被困住了,而是——我是城墙上的守夜人。
附一篇昨天写的文章。
《写在33岁生日》
一
小时候,祖母常常带我去舅公家。记忆中总是夏天,阳光灿烂,蝉声起伏,去舅公家的路很好记,沿着三溪港的堤道,顺流而去就行。
舅公家在北面。走在堤道上,左手是静静流淌的溪水,右手是默默生长的稻田。它们悄无声息地毫不引人注意,多年以后想起它们,才发现它们就是时间的样子:悄无声息地流逝,不知道有多少流入了大海;悄无声息地生长,收割了66次。
堤道的右侧伫立着许多老枫树,无一例外,统统被雷劈过。走几步路就会出现一棵,姿势千奇百怪。老枫树似乎成了一段段劈柴。有的从正当中劈开,这一劈给生与死划了条界限,一半绿意盎然,一半干枯腐朽。有的像做了个手术,老枫树敞开了胸怀,露出了空无一物的肚子。那粗心的医生忘了帮它缝起来。有的似乎差了点准头,斜着劈了一刀,那树像是无头的共工,只剩了幸存的一根小枝摇曳着几片叶子。
那条堤道仿佛是雷神炫技的展览会,我应该是最有兴趣的观众。我常常雀跃着跑去,抚摸老枫树身上的伤痕。我站在生死之界前,左手生,右手死。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是哲学,但这个意象被我深深印入了脑海。我钻进老枫树敞开的怀抱,抬头看见一线洞天,洞顶的阳光投射在泥土上,小小的树洞就像是一个道场。我数着“共工”身上的劈痕,一道,两道,三道……尽管它伤痕累累,但那根风中摇曳的小枝,依然那么倔强。
祖母看我这么痴迷,就适时地教育道:看到没有,这就是雷公发威的后果,你要听话,不然雷公要打。
说实话,我并不怎么佩服雷公。难道老枫树生长在那里,还不够听话吗?欺负人家不能动,不能跑,你雷公又算什么本事!相反,我很佩服老枫树,不管受了多少创伤,它们仍然努力生发新叶,温柔地站在路旁。人们看到它们,有人崇拜雷公的威严,有人嘲笑它们丑陋,还有一个少年,却另有一番感悟:逝水东流,生死一线。我们不过是死神镰下的稻田,何必那么在意丰收?
二
堤道是沙土路,多年雨水侵蚀,人畜践踏,车轮碾轧,它变得坑坑洼洼。然而这种坑坑洼洼并不代表颠簸。路面虽起伏不平,坑洼间却有着优美的曲线,好像泥土里长出了波浪。学会骑自行车后,我便总爱在这条堤道上骑行,轮胎碾轧在沙粒上发出清脆的毕毕剥剥的声音,起起伏伏间,我仿佛骑的不是一辆自行车,而是一匹骏马。后来在很多个梦里,我总会策马飞奔在这条堤道上。阳光明媚,云淡风轻,溪流潺潺,万物生长,老枫树如忠诚卫士守护我的梦境。
祖母穿着布鞋,走在堤道的正中间。对面来了人车,她便侧身一旁,让人过去,顺便看看来者是否相识。多半是相识的。如果是个汉子,打个招呼,各走各路;如果是个妇人,她们便会拉扯半天。碰巧妇人的村子就在近边,祖母还会被她拉回家里,泡上一碗自制的粗茶,将家长里短,陈年旧事,说个尽兴!
推荐阅读
- 速度 宇宙中比光速更快的四种“速度”,你都知道几个
- 男人帮 跑男、极限挑战、向往的生活,以这种方式“融合”!你期待吗?
- 召集人 张彬彬致敬李大钊,《28岁的你》正能量偶像解读伟人事迹
- 孕育 银河系中为何只有地球孕育出了生命这里告诉你答案
- 太阳 宇宙中所有星球都悬在空中,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这里告诉你答案
- 刘彦春 无论你负债多少,三年内都可还清所有债务!
- 地球 如果太阳燃烧完了,人类该如何生存?《方舟生存进化》为你解答
- 张震岳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加拿大paowang再添一锤,多人曝光记录
- 银河系 曲速引擎或能让人类飞出银河系,为何现在却无人研究?
- 铁矿石 全球最“值钱”的8大货币,美元直接垫底,前三名你们认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