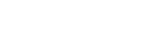考证缺陷,无疑会影响到黄氏兄弟的“河洛”解释与批评效果 。他们的“河洛”之说背后有着更为宏观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历史批评方面的追求,然据其“河洛”考证与解释是无法完全实现的,更何况他们的考证面临不可逾越的文献缺失,其考释也总被批评的意见、态度所牵系,遮蔽了所批评对象学说的客观实际、合理之处 。
“河洛”之说兴起于两汉,黄氏兄弟对汉代“河洛”之说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汉武帝时期,儒学获得官方主流地位,《周易》渐成首经,孔子成为至圣,加之“一字万言”的烦琐注经学风和符命盛行,学者们围绕经典和文献记载的“河图”“洛书”解说甚多,发挥更是不少 。在纬书大事敷陈之下,汉代“河洛”文献渐至丰盈,甚至脱颖而出,一度与《易》相配而立 。黄氏兄弟肯定汉人去古未远,流风犹存,训诂有信,但批评其“又不幸而为稗纬所混淆,大道沦于草莽” (黄宗炎:《周易寻门余论》卷上)。黄氏批评固有一番道理,但汉唐图书之说却不可一概否定 。尽管汉代文献在后世丢失、禁毁甚多,仍然可以勾勒出汉唐学者或文献中的“河图”“洛书”面貌,诸如来源、出世方式、地点、时间、频率、篇数、文本形态、字数、内容、性质、地位以及与《周易》的关系等 。汉唐学者于经书未尽处增以己见,是政治与经学发展之必然,对后世而言已经成为精神历史之实在,自有其价值意义 。但在黄氏兄弟和批评者看来,汉唐之于宋人的影响,是误导;宋人对汉唐的继承,则是误信 。这是因为,他们对汉代“河洛”资料的全面掌握、客观叙述、准确解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对“河洛”学说的缘起、原因、增益层次、价值意义等等缺乏足够探讨,从而对汉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功能、意义的认识流于简单化、表面化,存在理解偏差,遮蔽了汉唐图书文献背后具有的政治哲学、文化传播学、文献学、文本学等方面的学术史意义和理论思想内涵,进而在他们的理解中带有门派、门户之见,儒学思想上趋向保守,而文化上越发狭隘 。

文章图片
宋代“河洛”之学,不似汉唐铺陈构拟,而是深究其中潜含的经书思想的核心问题,并纳入理学论证框架 。朱熹、蔡元定等人采择汉人观点,吸收和转化刘牧、邵雍等人思想,建立“河洛”学说体系,其以图解经独出心裁,思考高度超迈前代 。第一,认为《系辞》“天地之数”即孔子发明“河图”蕴意 ,利用经籍文献和历史考证,把“河洛”图式及相互关系与天地之数、大衍之数、生成之数、奇偶之数、上下左右中方位、东西南北四方、五行、阴阳、八卦等要素综合为一体; 第二,将刘歆等人的“洛书”和“洪范九畴”,以及九宫之数,作为画图根据 ,并对比《河图》指出《洛书》之数、位、五行等配列特点,指出《洛书》乃“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 第三,认为《易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即“泛言圣人作《易》作《范》,其言皆出于天意” 。(《朱子全书》第1册,第211-216页) 由此,朱熹等人以“天地之数”作为经内之证,兼采历史上“河洛”诸说及可用之论,在其理学框架下创造性地建构出“河洛”学说的历史谱系和思想结构,形成“以图解经”为特征的综合创新 。黄氏兄弟的批评,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宋代图书易学的独特成就——不仅创造了“河洛”图式,还将之作为画卦作《易》之源的易学意义,延续孔子的易学思考,“以形象化的形式表达抽象化的内容,开创了全新的‘象’‘数’思维模式” 。(陈岘,第23页) 黄氏兄弟、毛奇龄、胡渭等图书学批评者虽然对宋代“河洛”学说乃至整体图书易学的问题进行有力批评,但并未提出更具思想性和创新性的理论,也很难在思想上彻底驳倒朱熹理学和由此建立的宋明新儒学 。

文章图片
以此观之,黄氏兄弟否定汉宋“河洛”学说,力辟图书之学和先天易学,乃至以朱熹为代表的官方儒学,仍是从儒家义理思想出发 (参见朱伯崑,第4册,第291页) ,吸取现实和近世社会的历史教训,担负守先待后之责,寻找文化之根本,构拟批判的政治儒学以解决精神上的空前危机,体现出反思的、批评的、超常规的学术特征 。二人把历史史实、文献作为批判工具,直接所求在于驳斥宋代图书易学与汉唐不同,确证宋人作伪;深层所指,是要批驳宋以来的朱熹一系的易学与理学,作学术史、儒学源流上的清理;最终目的,是以六经为准绳、历史为基础,建立新型儒学 。正如钱穆所言,“晚明诸遗老的史学,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理学’,亦可说是一种‘新理学’,他们要用史学来救世教人 。” (《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第29册,第6页) 只不过,黄氏兄弟所倚之考证,难以实现其理论阐说之目的,尤其当经义的真理性与它作为史实的真实性模糊不清时,“考据明而义理明”的障碍难以克服,“考据明”对“河洛”而言势不可能,而过度依赖经典历史语境化的论证方式,不利于其实现自身的理论诠释和价值诉求,不利于诠释显示经典的文本、历史、思想和解释行为背后的张力;黄氏兄弟的激切反思,有其对历史文化批评、反思的一面,却也局限于儒学经旨与门户攻伐,将有着丰富历史展开与思想蕴含的“河洛”之说扫落一隅,在“河洛”问题上缺乏充分的自省、自觉,恐怕也预示其新理学或新型儒学重建困难重重 。
推荐阅读
- 征婚|中国人是如何开始公开征婚的
- 星座|双子多娶妻、摩羯太苦命:中国人何时开始信星座?
- 《清明上河图》竟然泄露了北宋军事机密?
- 福布斯评选世界第一首富 竟不是盖茨而是中国人
- 古代官员雅好之癖 清明上河图曾被贪官纳为藏品
- 日本战败后《清明上河图》为何差点就到了日本
- 中国人的传统主食面条最早起源于哪个朝代
- 中国人在3000多年时间里 为何一天只吃两顿饭
-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有多少个人?
- 嘉靖“倭寇”实为中国人 在东南沿海得到民间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