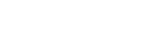12年前 , 31岁的博士毕业生姜鹏拎着行李 , 来到贵州省平塘县一个名为大窝凼的喀斯特洼地 , 他怎么也想象不到 , 眼前不通路、不通电、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大窝凼 , 几年之后会建起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FAST , 一个全球天文学家都梦寐以求的科研装置 。
那时的FAST , 在很多人看来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 梦想很大:口径500米 , 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 如果往里面倒满矿泉水 , 全世界70亿人平均每人可分4瓶;其目光所至 , 更是能“看穿”130多亿光年的区域 , 那将无限接近宇宙边缘 。 相应地 , FAST挑战之大 , 大到可以突破传统望远镜极限能力;建设条件现实之苦 , 苦到没几人愿意来实现这份梦想 , 即便是包括姜鹏在内的年轻博士 , 最初也一度怀疑这个项目“会不会是忽悠人的” 。
2016年9月25日 , “中国天眼”FAST落成启用 , 名噪一时;2020年1月11日 , “中国天眼”通过国家验收 , 投入运行 , 其综合性能是世界其他大型射电望远镜的十倍;2021年3月 , “中国天眼”已发现340余颗脉冲星……再也没有人怀疑大窝凼里也能实现梦想 。
如今 , 最早连接“中国天眼”梦想和现实的科学家南仁东 , 已经驾鹤西去;跟在南仁东身边见证FAST从无到有的年轻人 , 则继承了他的衣钵 , 坚守在西南深山之中 。 当从遥远的太空传来的电磁波落在群山环抱的大窝凼里 , 信号流淌进计算机集群 , 计算机沉默地跑着数据 , 身处大山中这群平均年龄才30多岁的年轻人 , 要从这个万籁俱寂的地方 , 让中国睁开“天眼”看穿星辰 。

文章图片
图为中国天眼FAST望远镜实景 。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起点
姜鹏 , 潘高峰 , 岳友岭 , 于东俊 , 孙京海 , 甘恒谦 , 钱磊 , 姚蕊 , 李辉……他们是“中国天眼”青年力量中的代表 , 他们中每一个人的青春 , 几乎都是在大窝凼里度过的 , 每个人围绕FAST都有一段长长的故事 , 而所有的故事都指向同一个起点 , 这个起点就是南仁东——FAST最早提出者之一 。
1993年 ,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 , 与会科学家提出 , 要在全球电波环境恶化到“不可收拾”之前 , 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 。
以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南仁东为首的中国天文学家 , 在会上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在中国境内建造大型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 而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不到30米 。
当时一个外国友人向南仁东发问:“你知道500米有多大吗?”他一下子被问住了 , 因为500米在大多数人心里都是数字 , 很难真正想象它的尺寸 。 南仁东说 , 这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好的一个问题 。
FAST口径达500米 , 其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8个“鸟巢”体育场 , 要找一个天然的洼地 , 远离大城市、射电干扰小的地方 。 那期间 , 南仁东走过数十个窝凼 , 周边县里的人几乎都认识南仁东——“一开始人们以为发现了矿 , 后来说发现‘外星人’” 。
2009年 , 姜鹏博士一毕业 , 就加入了FAST 。 他从学校刚到单位报到 , 就被车拉到北京密云 。 第一天和同事们抬着近500公斤的反射面板 , 从东边跑到了西边 , 几个博士疑惑 , “我们以后不会就干这个吧?”
也是那一年 , 负责观测规划和数据格式技术支持的钱磊 , 也加入了FAST项目 。 他至今记得 , 当天南仁东请他和同事在食堂吃了午饭 , 聊了未来的工作 , 算是简单的欢迎仪式 。
没过多久 , 他们被拉到了FAST的台址 , 那是“中国天眼”的“眼窝”所在 。 有人感慨道 , 未来 , 神秘的天文发现将从这里诞生;也有人感慨 , 他们所有人的青春 , 都要围着这口“大锅”转了 。

文章图片
图为“中国天眼”FAST研制团队的部分成员 。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
那时 , 刚参加工作3个月的于东俊去现场进行FAST首级控制网稳定性监测 , 需要在4个山顶上放置设备采集数据 。 那是他第一次出公差 , 第一次坐飞机 , 第一次去山清水秀的贵州 , FAST诞生地的神圣画面在他脑海中幻想了无数遍 。
“可到了现场 , 才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 吃住就在建筑工地搭建的临时板房里 , 身上布满了蚊虫叮咬的红包……”于东俊说 。
大窝凼被丛林覆盖 , 极其陡峭 。 第三天 , 这位生长在平原地带的小伙儿 , 背着30多斤的设备去现场采集 。 山坡中腰有一个坡度近90度、高4米的大石头 , 仅有三个凸起部分可供借力攀岩 , 于东俊用左手抠出石头缝隙 , 身体重量压向左侧 , 准备发力 , 但没想到 , 借力处由于喀斯特地貌常年风化已接近脱落 , 身体瞬间失去重心 , 出于本能反应 , 他右手顺势抓住了一个树枝 , 借助树枝的力落到了大石头下面仅10厘米宽的落脚地 , 右手被树枝上乱刺划出了血……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 如果没有树枝 , 身后便是10多米高的深渊 。 其中的凶险可想而知 。 ”于东俊说 。
【天眼|从“中国天眼”看到青年力量】从1994年选址到2016年FAST正式建成 , FAST团队用了整整22年 。
姜鹏有时开玩笑说:南仁东先生挖了一个大“坑” , 把一百多人都装进来了 。 也正是这一百多人 , 把大窝凼变成了一个现代机械美感与自然环境完美契合的工程奇迹 。
第一
FAST的设计从一开始便是史无前例的 ,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 如何设计 , 如何实现 , 建成之后如何调试 , 以及如何使用等等 , 所有的难关都只能靠自己 。
“中国天眼”的设计不同于世界上已有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 这首先体现在“视网膜”和“瞳孔”的设计上 。 “视网膜”指反射面;“瞳孔”指馈源舱 , 即放置接收宇宙外信号装置系统的舱体 。
作为世界首创 , “中国天眼”的“视网膜”是主动反射面 , 可以改变形状 , 一会儿是球面 , 一会儿是抛物面;“中国天眼”的“瞳孔”也更为“灵动” , 采用全新的轻型索驱动控制系统 , 可以改变“瞳孔”角度和位置 , 有效地收集、跟踪、监测更丰富的宇宙电磁波 。
40岁的潘高峰在FAST团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 是负责大跨度柔性六索并联机器人的研制及建设:一个30吨重的馈源舱 , 要利用6座铁塔支撑6根钢丝绳悬吊 , 通过同步收放钢丝绳 , 拖动馈源舱在直径为206米、高约140米的球冠面内进行运动 , 实现48毫米的定位精度 , 姿态角小于1度 。
“匪夷所思的精度控制 , 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 ”潘高峰和团队成员研制出耐10万次弯曲疲劳寿命的动光缆 , 这个成果达到了相关要求的100倍 。
潘高峰时常慨叹:在FAST的建设过程中 , 经常会遇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绝境 , 但有时也能享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 。
创新的过程中 , 没有人能给年轻人一个标准答案 。
2005年 , 孙京海还是南仁东的研究生 , 便加入FAST团队 , 参与馈源支撑系统的仿真和实验研究 。 在工程建设期 , 他多次分享仿真经验方法 , 这一从未被尝试的方法受到了质疑 , 他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你如何证明自己的仿真结果是对的?
苦于没有原型的实践验证 , 孙京海没法证明自己的方法 。 后来 , 他有机会承担了控制系统调试的任务 , 为了尽快实现控制指标 , 他独自重写了几乎全部核心算法代码 , 没时间吃饭就不吃 , 需要赶进度就不睡觉 , 五天五夜的调试 , 就为了证明自己的方法是对的 。
验收当天 , 所有指标一次通过 。 孙京海说 , “那一晚才是睡得最香的 。 ”
2017年10月10日 , 在北京四环外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大楼里 , 由FAST捕获的首批脉冲星信号第一次向外界展示——“嘟呜嘟——嘟呜嘟——”“嘟——嘟——”这是来自1.6万光年外和4100光年外的脉冲信号 , 像是成年人的心跳 , 短促而有力 。
这两个声音 , 让中国实现了一个“零的突破”: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天文设备第一次发现脉冲星 。 享誉世界的澳大利亚帕克斯射电望远镜的科学主管乔治·霍布斯评价:这是国际天文学界目前最令人激动的事件之一 。
情怀
说起FAST当年勘察台址 , 潘高峰想到这样一个画面:那时 , 南仁东常和年轻人一起 , 在没有路的大山里攀爬 。
在最陡峭的一个山顶前 , 大家都劝时年65岁的南仁东在山下等着 , 看完结果向他汇报 , 他却要和大伙儿一起上去 , 看看实际情况 。 南仁东这么大岁数还要亲自上去踏勘 , 搞得在场几个设计院的老总也不好意思 , 纷纷跟着爬上去了 , 其中一个院长还穿着西装、皮鞋 。
那一年 , FAST遇到了一次近乎灾难性的波折 , 即索网的疲劳问题 。
姜鹏记得 , 那时他们从市面上买了大概数十根钢索进行实验 , 却没有一根能满足要求 , 于是他们不得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钢索疲劳性能实验研究 。 他说 , 这可能也是新中国以来 , 能查到资料范围内最大规模的一次索疲劳实验 。
索疲劳实验枯燥、耗时长 , 在北京 , 在武汉 , 在广西 , 全国不同的地方开始实验 , 两年多的时间 , 这群年轻人把FAST最严重的一次技术风险给解决掉了 。
43岁的甘恒谦负责FAST电子电气设备的运行和维护 , 在他看来 ,FAST团队就像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 , 以南仁东为代表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 , 坚持自主创新 , 新人一代代地跟上 , 攻克了众多FAST建造技术难题 , 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现在的“中国天眼” 。
在这支队伍里 , 挑战权威是被允许的 。
37岁的姚蕊曾面临馈源舱超重问题 , 馈源舱接口多 , 设计输入多 , 为了确保整个馈源支撑系统的安全性 , 馈源舱的重量阈值是30吨 , 而馈源舱的详细设计一度重量超标到34吨 。 一个颠覆性的想法出现 , 推翻馈源舱设计方案 , 将馈源舱的圆柱体变成了“钻石三角形” 。
这意味着前期的工作都被推倒重来 。 姚蕊拿着方案给南仁东看 , 心里忐忑 。 南先生看了一会儿没说话 , 过了一会儿道 , “好像也不难看 。 ”
就这样 , FAST的外形与布局被重新设计 。
直到现在 , 姚蕊都不知道当时南仁东觉得“钻石三角形”的馈源舱是好看还是难看 , “但他让我们做了新的尝试 , 让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 。 ”
2016年9月 , FAST项目落成 。 南仁东和两位朋友合影 , 一旁的友人笑容灿烂 , 但南仁东眉头紧锁 , 皱成“川”字 。 他知道 , 项目落成远远不是结束 , 而是新一轮挑战的开始 。
“中国天眼”直径500米 , 却要实现毫米级的精度 , 难度相当大 。 他带领的这批年轻人 , 还要在漫长的时光里 , 在大窝凼与技术作斗争 , 与寂寞作斗争 。
曾有人问潘高峰 , 像你们这种单位 , 挣钱少 , 出差多 , 也顾不上家 , 为啥还待在这儿?当时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 只是觉得在这儿工作氛围舒心 , 干的活也非常感兴趣 。
直到后来 , 他听到一个词——“情怀” , 在他看来这个词很准确地形容了他们这群人 。 他们身上有着深深的“科学情怀” , 因为此才有那么多的人能够耐得住寂寞 , 坐得住板凳 , 能在大窝凼坚守下去 。
接力
如今 , 大部分的亲历者已经记不清FAST最初建设时有多苦 , 他们在零星的记忆里拼凑出当时的画面:那时没有板房就睡帐篷 , 被褥里可以挤出水 , 有人起了一身的红疹;水质不好 , 没法洗澡 , 只能拿毛巾擦一擦 , 有时一待就得20多天;有了板房 , 雷雨天一来 , 一个雷电下来 , 好多设备就被雷击坏了 。
苦吗?难吗?姚蕊参加FAST项目已经将近16年了 , 青春的年华都奉献在了大窝凼 。 她说:“参加到这样科技重器 , 不枉少年 。 ”
在姚蕊看来 , 年轻的时候就要抛开世俗欲望 , 要立大志入主流 , 上大舞台做大事 , 做对个人和国家发展所需的事情 。 她庆幸自己能将个人爱好和国家需求结合在一起 。
姚蕊期盼着自己慢慢成长为南仁东先生的样子 , 在这里坚守下去 。
打扮得像个背包客的岳友岭 , 可以从FAST讲到脉冲星再讲到黑洞 , 绕一圈再讲回FAST , 连续讲两个小时 。 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留在FAST , 他拍着大腿说:“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 特别有趣!就是……就是你小时候学过的那些事 , 现在终于可以自己亲手做了!”
2021年3月31日起 , FAST面向国际开放 。
三代人倾注20多年青春的FAST开始眺望宇宙:基于FAST数据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已有70余篇 , 所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超过340颗 , 是同一时期国际上所有其它望远镜发现数量总和的3倍以上 。
12年过去 , 姜鹏已经成为FAST团队的“老人” 。 想想自己从20多岁蹦蹦跳跳的小伙子 , 到现在FAST项目的总工程师 , 他说 , “如果真的有一天 , 我们这群人不能再为FAST做更多的贡献 , 我们要学会放手 , 要扶持更多的年轻人 , 继续接力下去 。 ”

文章图片
在4月22日举行的一场媒体沟通会上 , 姜鹏向采访人员展示了一张团队合影:100多人的团队 , 用了20多年的青春 , 铸就了中国利器 。 如今老一辈的人大多逝去 , 青年一代成为主力军 。
这张团队照的正中间 , 是南仁东 。
恍惚之间 , 姜鹏好像又回到了多年前 , 听到南仁东对他说:姜鹏 , 你在哪儿 , 你给我过来 。 “他永远都那么地不容置疑 , 虽然我经常反抗他……”
推荐阅读
- 快报|“他,是能成就导师的学生”
- 技术|“2”类医械有重大进展:神经介入产品井喷、基因测序弯道超车
- bug|这款小工具让你的Win10用上“Win11亚克力半透明菜单”
- 重大进展|“2”类医械有重大进展:神经介入产品井喷、基因测序弯道超车
- 历史|科普: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探索宇宙历史的“深空巨镜”
- 空间|(科技)科普: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探索宇宙历史的“深空巨镜”
- 样儿|从太空看地球新年灯光秀啥样儿?快看!绝美风云卫星图来了
- 精度|将建模速率提升10倍,消费级3D扫描仪Magic Swift在2021高交会大显“身手”
- 四平|智慧城市“奥斯卡”揭晓!祝贺柯桥客户荣获2021世界智慧城市治理大奖
- |南安市司法局“加减乘除” 打造最优法治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