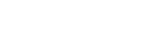惠英红为啥一直没结婚
何惧生老病死,情不得善终;未能举案齐眉,终究意难平。梗概是微博上看来的
细节是我瞎掰的
第一句是我矫情的
发出来是想让你点赞的
下面是正文
﹉﹉﹉﹉﹉﹉﹉﹉﹉﹉﹉﹉﹉﹉﹉﹉﹉﹉﹉
阿英扎着两条粗黑的辫子,面黄肌瘦的脸.上偏生着一双明亮的杏眼,这双眼睛会识人,因此在这片红灯区售卖杂货的孩子里,阿英的生意总是最好。从3岁到11岁,阿英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界已经摸爬滚打了八年,她出落的一天比一天漂亮,见过她的人都不安或不善的揣测,她是否早晚也会被归拢到这片红灯区里。咸湿的海风携来码头上的嘈杂与热络,是与阿英灰蒙蒙的日子不相干的瑰奇。
买孩子们的杂货的人往往不是土著居民,而是那些金发碧眼的美国大兵,他们永远高谈阔论、永远开怀大笑,很喜欢在这些小孩这儿买一些口香糖和烟之类的小玩意儿,出手又通常是带着同情值的大方,因此孩子们都很喜欢跟大兵们打交道,阿英也如是。其实同质性使得这些深眼窝高鼻梁的人在孩子们眼里并没有什么差别,而那个手里总是握着一张报纸的大兵就在这无差别里闯进阿英的视线来。
他手里的报纸都是当日的晨报,尽管每个孩子的杂货箱的万宝路无甚差别,他的香烟却永远只买阿英一个人的。付钱时他习惯用蹩脚的粤语向阿英询问报纸_上的某个字,见阿英沉默的摇摇头就露出一点遗憾的神色来,可明天再接过万宝路时他还是会用烟盒抵着铅字轻声说“请问这个是什么字”?
“请问这个是什么字?”当这句话轻轻落在头顶时阿英头一次感到莫名的窘迫,好像自己是正午时屋顶_上晒得弯曲的红薯干,最可怕的是,这窘迫每天都要经历一次。被问上几次后阿英开始在卖东西的闲余找一点路人丢下的报纸,她不想让其他的孩子看见,就将报纸叠成四四方方的小块塞进杂货箱的角落里,到家后再拿到父亲面前展开。
阿英的父亲是个没落的秀才,没有讨生活的本事,但肚子里的书袋不少。阿英每日跟着父亲在报纸_上学一点字,日子久了大兵再问时,阿英偶尔也可以对,上他的眸子轻声回一句,这时大兵就露出欣喜的笑来,他笑,阿英也跟着笑;阿英笑,他也跟着笑。他们开始偶尔交谈,大兵会跟阿英讲码头上的新闻,讲她听不懂的他的国家在中南半岛的战事,他的粤语讲得实在不怎么样,以致阿英每每想到也会发笑。这个素来聪慧的女孩还不知道,想到一个人时没有缘由的笑便是每个少女情动的开始。
美国在中南半岛的战事开始吃紧,大兵的烟买得不再那么勤,三五天才会来这里一次。七月的香港是很热闹的地方,阿英的生意也格外好些,她就是在向一群游客推荐口香糖时被喊住的,大兵今天手里难得没拿报纸,他一下子买了十盒口香糖。“明天我得走了,要上战场了”,他用平常拿报纸的那只手挠了挠头,又说“其实我不抽那么多烟的,在你这里买得烟也许够我抽到今年冬天,希望那时战争就结束了,而我可以回到这里,继续来买你的烟”。阿英想问他点什么,但喉咙被什么堵住了,除了“好”字什么也说不出来。大兵半蹲到和她一样的高度又问“你知道我爱你用粤语怎么说吗”?在喧嚣的海风里,大兵说“我爱你”。阿英第一次听到有人用粤语跟她
说“我爱你”,原来粤语这么好听,好听到可以让人说不出话来,阿英想。大兵似乎也并没有想得到什么回答,能在她清亮的眸子里看到自己,他已经很高兴了,随即将10美元放进阿英的杂货箱里,边走边冲她摆摆手说“再见”。
阿英始终讲不出一个字,她将10美元紧紧攥住,跌跌撞撞的走回家去,到家喝了一大碗加了砂糖的姜汤就立刻睡下,她好像生病了。
没了大兵们的码头和红灯区比以往沉寂了一点,孩子们的生意也不那么好做了,阿英每晚都会将大兵临走前说过的话从回忆里找出来擦拭,孩子里偶尔会有人感慨以前大兵们的阔绰,除此之外,他们存在过的痕迹似乎都被海风冲撞得--干二净,直到冬天结束,战争还没有结束,阿英也没有在码头上等来她想等的人,她直觉得相信他不会泯灭在战火里,可消息却又无处可寻。
大兵走的第二年阿英也离开了这片红灯区,她是有傲骨的姑娘,从来都不属于这里,她从夜总会的舞女做到影视公司的签约演员,但从不忘抽空就回码头看看。无论做哪个行当,她永远是最努力、最出类拔萃的那一个,她在演员这条路,上走得很久,久到大红大紫、大起大落都仿佛成了昨天的事,也许再过几年她会拿到一个终身成就奖,在一片赞叹声里功成身退。然而这么多年她还是子然一身,风云雨霁无人叨扰,喜怒哀乐也无人分享。
推荐阅读
- 地球 设计寿命20天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已飞了50年,何时回收?
- 中国网 【探秘延安红街之二】藏在延安红街里的八个故事
- 萌探探探案 杨紫cos红孩儿超可爱!一旁那英却成焦点,扮铁扇公主笑翻网友
- cp 孟子义“黑红”之路一去不返!调侃张翰不会做饭,与郭麒麟硬炒CP
- 红包 两人的感情真好!《创4》龚俊透露张哲瀚发红包让他给吴宇恒撑腰
- 红孩儿 《萌探》全员COS西游记,杨紫神还原红孩儿造型,确定是28岁吗?
- 红孩儿 《萌探》最新路透曝光,杨紫造型再出圈,喜剧效果却在杨迪身上
- 东方红一号 能量耗尽5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为何还没坠毁它还能再飞100年
- 笑点 离开黄渤后,孙红雷新综艺又迎来爆笑搭档,组合名够我笑一天
- 龚俊 《中餐厅5》来了!丁真加盟,爆红男顶流当厨师,但女嘉宾没看头